电影诞生了100多年,但关于电影本质的问题却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让我们在数字技术非常发达的21世纪深思。
琉米爱尔在法国巴黎咖啡馆放电影,黑白无声,开头12帧,结尾24帧。我们称之为电影。然而,今天的电影是一个彩色的圆形立体,每秒钟有2000多个相机用于实验。它捕捉子弹穿透甲板时产生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中国第一部不用拍摄的全数字电影是由电脑和电脑制作的。计算时综合了最漂亮的人的鼻子距离、眉毛距离和肩膀距离。如今的电影显然不是靠机械拍摄、化学摄影成像、印刷完成的,而是越来越多的可以完全摆脱电影摄影机的电影。与以纪录片美学为主导的传统时代相比,电影进入了以科技为主导的影像美学新时代。
技术似乎无所不能,让电影成了“真实的谎言”
如今,我们特别关注多媒体和新媒体时代影像创作的总体思路,而不仅仅是创作一部院线电影或电影电影,并将其纳入单一的电影制作和教学研究框架。卢卡斯创立工业光魔公司就是为了拍摄《星球大战》。他将电影的特效从传统的模型制作和关键技术中解放出来,开创了利用计算机数字技术完成电影构思的新途径。后来,他创造了许多电影类型,尤其是拍摄了一系列“银河电影”。103010制片人来中国开会的时候,有人问他,拍这样的电影,电影行业还剩下什么?他们回答并讲了一个好故事。他们把《星球大战》看作是人性的史诗,而不仅仅是科技和高科技的产物。
我们还应该记住,在卢卡斯同时代的人中有一个“罗马俱乐部”,它公布了一个增长极限和一份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指出人类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并没有被科技从根本上改变,被视为救星。如今,推动消费指数增长的基础,恰恰是人们无法满足的欲望。我们现在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以我们应该回头看看科技高速发展给电影留下的痕迹。我们不仅要看到科技对电影的推进,也要反思科技对电影的一些负面影响。
德国电影理论家艾因达姆最早呼吁捍卫电影艺术的纯洁性,他因坚守无声电影影像的美学品质,长期被视为电影美学保守主义的典范。他反对声音进入电影,想要保证一个所谓的画质(电影语言)的纯净。艾因达姆对图像本体的辩护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有价值的预见。当时他并没有无缘无故提出这样的观点。当时,声音肆意渗透到影像中,给电影世界带来了令人作呕的灾难性影响,声音在精心设计制作之前就淹没在影像中。因此,屏幕上的尖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各种噪音,当然给曾经寂静的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噪音。
曾经,电影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观众的心理作用,观众确信屏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二维图像创造了一代或几代人对电影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它已经进入了一代又一代电影观众的观看体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对假想图像感兴趣的动物。科学家们做了实验让鱼去看电影。当鱼意识到图像是假的,鱼就会离开。但人是不一样的,知道图像是虚构的、假设的,还是会被它们迷住。因此,当数字技术、3D动画技术,尤其是VR技术进入电影观看过程中,电影与观众之间建立的默契开始瓦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3D屏幕空间,同时也提醒我们3D影像空间是虚拟的、假想的。比如《星球大战》的画面,很多用数字技术拍摄的镜头一目了然,观众也明白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假设的。这种默契的打破不是因为简单的技术原因,而是强化了我们对假设的认知。鼻子上的立体眼镜总是提醒观众看一部虚拟的电影。
因此,我们曾经惊叹于艺术的迷人魅力,但现在我们惊叹于科技无所不能的技能。过去,我们为银幕上真实的表演而流泪,但现在我们为电影中的奇迹而哭泣。数字技术让我们远离作为艺术的电影,或者让我们更接近作为奇迹的图像。观众有自己的体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电影能够通过高科技数字技术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逼真影像时,电影与生俱来的记录本质或者说相机不会说谎的真实神话已经被击碎。这部电影似乎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以假象制造现实,须理性看待银幕“奇观”
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电影,我们不再相信它们其实是用电影摄影机拍摄的,而只觉得技术很难。数字技术使展示无与伦比的创造能力成为可能。电影不再用现实反映现实,而是用虚假现实创造现实,用虚拟技术模拟现实,无限延伸人类的想象世界。数字技术会给电影带来哪些可能性?人有限的想象力能否满足其无法无天的创作欲望?一切都在进行中。
心理学告诉我们,观众的“自虐心理”是电影事业最大的助手。这种“自虐心理”的表征是,电影的欺骗程度越高,越逼真,越相似,观众越满意。观众讨厌看得见瑕疵的电影,讨厌表演不切实际的电影,所以现在我们的眼睛和头脑显然是同时被数字技术带入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影像预设和调控的境地,不仅无法自拔,还要不厌其烦地为电影买单。虚拟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游戏和想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远离我们自己的客观认知。
现实世界。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个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的“自我虐待”的心理建构的历史之途?我们是甘愿被它所左右、所控制,还是要从一百多年的怪圈里面走出来?这里所说的走出来,不是指我们拒绝电影、反对电影、否定电影,而是要从一种原始的、迷醉的、癫狂的电影观影障碍当中摆脱出来,最起码在理论的判断纬度上,能够冷静面对我们现在的电影,而不再是不加分析地为一些变术、骗术、妖术而欢呼。电影技术发展所提供的银幕奇幻,在思维模式上,实际上让观众回到原始人图像思维的阶段。然而,现在人类无可挽回地进入到电影自行运行的逻辑里面,这个逻辑里面有我们所热衷的娱乐、迷恋的幻影、白热的梦想,这当然都是我们需要的。但科技影像带给世界的负面因素已经被无数的事实证明,其中科技也难辞其咎。好莱坞早期电影禁止在一个画面里人对人开枪,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人对人的射击,而且是对优艾设计网_平面设计已经投降缴枪的俘虏的射击,这是电影伦理非常关注的画面,这种画面在中国电影里越少越好。
我们不能让“商业”替所有的电影受过,说电影是一种商业,它要卖钱,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忽略不计。但是谁让杀人的情节越来越逼真?是利欲熏心的片商,还是鬼迷心窍的编剧、唯利是图的导演?就算我们可以把电影的罪孽全部归于人的力量所为,在技术层面,我们还是无法将暴力的罪孽推得一干二净。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曹聪讲,科学家的研究是好奇心驱使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不全是为了利益。但是这种好奇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以被彻底阻断吗?可能不行。在电影里,科学技术帮助人们实现了更多观察世界的可能的同时,也助长了影像与生俱来的原罪。我们不能说科学技术害了电影,可是电影这个曾经被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世界,现在确实被科学技术所改变,我们在三维动画技术的引领下看到了天宫、仙境、乐园的同时,也看到了魔窟、地狱,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电影的记忆变成恐怖的记忆。
科技助推电影,但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
技术的建树全依赖于科技吗?电影叙事的疆界,曾经是依靠科学技术来开拓的,但是电影艺术的建树却很少因为技术的驱动实现,艺术的创造有时甚至恰是在技术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有限的科技条件甚至还激发了艺术家的审美想象。当年,中国第五代导演组成两个青年摄制组,一个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一个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拍摄条件和技术水平、资金远远不如当下,但是这两个摄制组创造了《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这些青年电影人当时的技术条件非常有限,包括贾樟柯,当时冲印他早期作品胶片,用的是北京电影洗印厂别人冲完以后剩下的药水,可是这种简陋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妨碍他最后走向国际舞台。
所以,科学技术对电影的推进并不能被绝对化,更不能用一种技术结论的立场,判断整个世界电影史。科技毕竟仅仅是电影的工具,决定电影进步与发展的必定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合力所致。单一的科学力量,只能够为电影带来动力,并不能包揽电影历史前进的全部荣誉。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恰恰来自于对科学主义的治理。在科学主义看来,迄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包括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最终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也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定义,从而将科学推向了一种绝对化境地,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不仅荒谬可笑,其结果不仅会使原本科学的学说变成类似于人类于宗教的迷狂,且有可能使我们葬身于教条主义的深渊。在传统电影的发展进程中,科技对影像的历史性再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不得不将推进电影艺术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正向力量,与它的负面效应区别对待。这种理性,将驱使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改变人类审美世界的技术、变数分别讨论,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
蕾切尔·卡逊最先发现农药的致命危害,写了《寂静的春天》,美国现在的环境署就是根据蕾切尔·卡逊的告诫成立的。这本书以诗性的语言告诫人类,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在科学实验室里面发明的农药进行干预和禁止,那么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人类的春天将失去如歌景象,而陷入一片沉寂的恐怖之中。世人熟悉的尼尔·波兹曼写过两部惊世骇俗的电视批评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问题。他反对用技术代替人类思考,反对技术至上主义。
蕾切尔·卡逊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曾经警告人们,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对自然界的世界是这样,对于升级换代越来越频繁的银幕世界来说,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电影母体和电影生命的组成部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科学自身的问题在电影诞生之初就被带入电影的机体当中,如果它有问题,它被带入电影也已经一百多年了,问题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究竟是在改变电影的技术手段,还是在改变电影艺术的艺术本质。它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还在迷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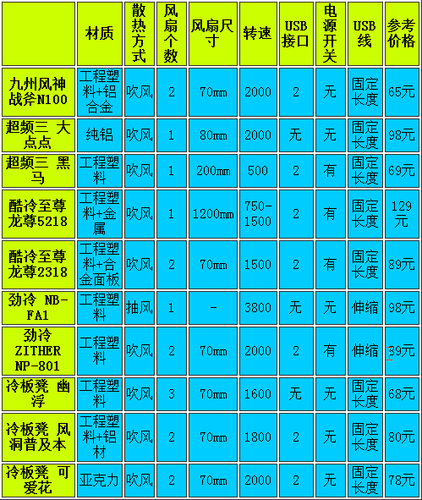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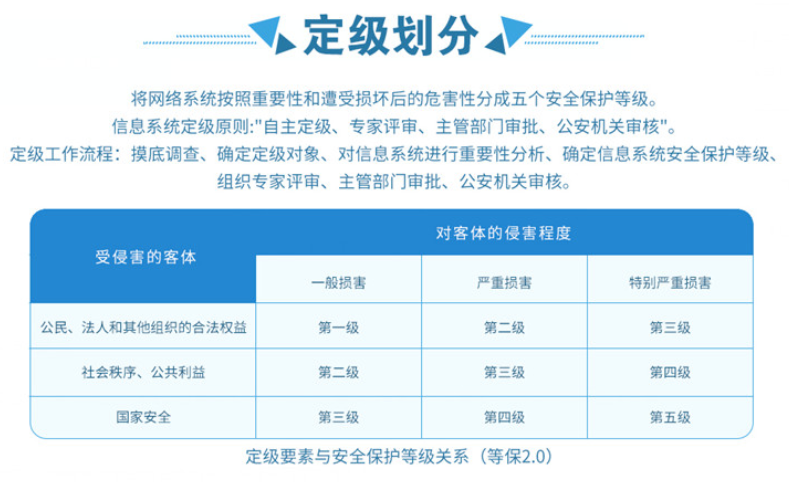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